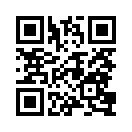一夜之间,一场雨浇淋而下,不大,细如牛毛,缠绵霏霏,温度也顺势玩了个滑梯,让我从初夏坠回了冬天,无可奈何地在T恤外面套**外套。说起来,这种湿寒才是冬天本应该有的样子,前几天20几度的高温实在有些不太像话了。
我像之前一样,打开房门,拖过去凳子,做作地泡了茶,倚门看书。昨天、前天以及大前天的那种被太阳晒得懒洋洋而顺手拿到书就看的感觉不见了,我开始纠结该看什么。翻了两页《群山回唱》,没能看下去,那一段夏日的阿富汗——酷热、沙尘、混乱,太不应时应景了。我又换了《预知梦》,看到五月里,草雉休假在家的场景,也不想看下去了。最后,我挑了《五颗桔核》——一个雨中的案子,总算一口气看完了。
按照之前的感觉,我总以为,雨天是最适合看书的时候。因为下雨,所以我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不出门,而在家里看书了。大晴天窝在家中,有时难免有一种违和感,继而有些愧疚。在这样的一种湿寒的环境中,我不想出门的感觉是很强烈的。记得小时候,尚读小学,就有湿寒之中仓惶地从学校逃回家的经历。一回家就冲到房间里,也许爷爷奶奶正在看什么京剧的碟片,而我拿着书,倚着窗户看。
当时,别说是那京剧的唱声,就算是炮仗冲天、烟花怒放,也休想把我从那看书的状态中打出来。而现在,很不幸的是,迎面而来的一阵风就让我缩了缩脖子,书中不应景的片段就让我摇了摇头。当时的不论何时、不论何地都能进入的状态,现在看来,只有晚上才会出现。即便是非常对胃口的书,也不是想想就能进入一个好的阅读状态了。
偶尔有人想看书了,会让我推荐推荐。以前我一碰到这种情况,就会很兴致勃勃地说出一本甚至是十几本来。那些不是让我保持着一个癫狂颤栗的状态读完的,就是现下正一头栽进去而未曾出来的作品。可是,我发现,推荐的结果往往不尽如意。一些让我留着哈喇子去期待的书,有时却被冠上不好看的评语,哪怕是畅销书也会遭遇这样的尴尬。
现在,谁要是让我推荐书籍,我就会很谨慎了。因为我很清楚一下子说出一堆或者是一味地推荐自己喜欢的作品,很容易让对方失望,换言之,很难看得下去。对于那些曾与我合作营造出全身心浸入的阅读状态的书籍,并不是都符合其他人的胃口的。有时,我那不吝赞词的推荐,会让翻了几页的对方感到失望,也许他期待过高了,也许他像我现在这样没能进入一个良好的阅读状态。
不禁让我感叹,状态这东西的确很玄妙。斯蒂芬·金说他不在黑暗的周遭环境中,不在那个小房间里的小桌子前,他就写不出小说。这是一种写作的状态。我想这与阅读状态殊途同归。也许就如我一般,日渐浮躁,环境稍一变动,就无法安静地看书。一些作者也一样,因为时间与经历的缘故,尽管才华横溢,但是写作的塑性却慢慢的僵硬了,只有特定的环境才能将之全面唤醒。
说写作这么一个创作或者是再创作的过程仰赖于环境所给予的状态,那肯定是偏颇的,因为状态的根源还是在自身。但是,状态所给出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很多作者都清楚,状态对了的时候,手中的笔就仿佛是自己在动一般——脑中萦绕着画面的路易斯、观看日出的罗曼·罗兰、戴着耳机子的莫言。
我一直在想,如果有一天,所有的读者状态都不对了,这些著书的作者们该作何感想?没有人看的作品到底有没有价值呢?我知道我这个想法是很偏狭,甚至是很没见识的,但是,这无形之中也契合了那句老话——好的作品是作者和读者一同完成的。如此想想,在我的假设之中,再好的作品也都只是光杆司令了。
其实我是明白这个问题的答案的,一番自我饶舌之后。首先,这个假设永远都不可能成立,即便我的脑子不好使了,懒得看书了,那也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如此了。其次,也是最关键的,作者们到底是为什么在写作,真的是为了读者们吗?
为读者而写作,这其实是一个很光鲜很好听也很实际的说法。确实,对于很多仰赖于写作生存的作者来说,读者乃是****,为读者写作,也是在保饭碗。写读者爱看的作品,这句话无论何时何地抛出来,我都没法辩驳,即便是迎合某些读者的某些胃口的某些作者,一切为了生存。我们暂且抛开这某些吧,虽然人数不少,但我不想讲他们。
剥离之后,人数缩水了很多,但是,我想,这些作者们也都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有一定数量的读者,甚至是能给这之中的一些读者带来疯狂的阅读快感和淋漓的思想洗礼的。这是必然的。然而,这又必然不是全部。姑且不论马尔克斯、格拉斯、村上春树这些不但拥有数量而且拥有质量的读者的作家们,另一些人却是没有这样的好运。我的脑中排队似的出现了巴尔扎克、卡夫卡、普鲁斯特这些人的身影,但随即我又摇头了,诚然他们生时没有大批量的作者,但是时光滚滚到现在,他们的读者比谁都多。
我的脑中开始充斥着这样的饶舌,一批批人的身影出现,又一次次地将我带入了更大的困惑。能够到我脑中排队的作者,换言之,以我的见识,所能熟识的作者,现如今又有哪一个不是名声如霹雳?又有哪一个不是拥有极大基数的读者群?于是我又执迷不悟地寄希望与一些默默无闻的作者。几番纠结,我最终归向了我很早之前就已明白的原因——永远不要将一个人的创作动机给钉死,为自己抒情、为掏些肺腑话、为谋生路、为取悦他人、为打响名声以及纯粹为了读者和更多其他,谁又能说哪一样没有成为过一个人作者的创作动机呢?
这是我习惯性地为自己想不出结果的问题套上一个既定的答案的毛病,不过这回我想我并没套错。问题一开始就是不对劲的,不断思索下去,用老和尚的话说,那就是着相了。况且,我只是我,我又怎么可能知道千千万万的作者的创作动机?我所最知道的是,他写得欢快,我看得开心,他写得真挚动人,我看得感动涕零,这就是最完美了的。退一步讲,他写他的,我看我的,这之间的关系浑然天成,何必用曲为谁唱这样的问题来对之进行自以为是的切割呢?
雨还在下,阳台的栏杆上满是小水珠。我猛然想起之前泡的茶——冰凉的茶还真难喝!我突然觉得,我今天能够把《预知梦》一口气看完了,就在这*雨霏霏的湿寒之中。
本文作者:青衫磊落
公众号“启程制造”。